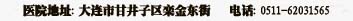编者:本文作者斗笠哥以湖南为样板,深度调研土地变革形势,系统分析了当前农资行业各种热门话题,对农资行业人士了解行业动态、分析行业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前言
湖南的统防统治、土地流转、合作社的兴起、家庭农场的建立,甚至是合作联社的出现走在了全国的前沿。尽管存在被动抑或主动,这其实都是湖南农民一场有关于土地的变革,其结果就是土地在集中。参与不参与的人们都不得不思考,土地由谁主宰,土地由谁耕种,如何提高生产水平,如何创造剩余价值。笔者通过两年多的调研和所见所闻,对有关湖南农民土地变革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供有关部门和业内人士参考。
我们从01年9月1起至年9月7日,共11天,在湖南汩罗、平江、浏阳、洞口、隆回、双峰、新宁、株州县、攸县、祁东、祁阳、邵东、邵县、湘乡、东安、武冈、道县、醴陵、汉寿、湘阴、望城、长沙、宁乡、南县、沅江、临湘、炎陵、城步、绥宁、华容、君山桃江、安化、临武、新化、涟源、岳阳县37个县(市),近多个乡镇,对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种植企业和农民进行走访,听取和收集了他们的反馈。许多农民对土地的理解和概念,与我们这些在城市呆在办公室所想的大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笔者与多位知名企业高层交流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土地流转不会那么快,很多农民有土地情结,不会放弃自己的土地。而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越有土地情结的人,更容易把土地流转出去,其实原因很简单,真正有深厚土地情结的人,是不会看到土地荒废的。而那些对土地没有感情的人,往往会以“反正我不靠这几亩地赚钱”的心理,而占着土地不耕种。还有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以湖南湘中、湘北为例,一个村约多户,平均每户4~5人,一个村约~口人。水田面积平均0.5~1.5亩,湘中相对要多一点,平均有1.亩左右,湘北平均少于1亩,而湘南平均约0.5亩。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大致可以测算一个行政村可耕种的水田面积约1~亩。接下的问题是这些土地未来将由谁耕种。50后是60岁以上,60后目前是50多岁,70后是40岁,80后是30岁左右,90后是0来岁。80后愿意呆在农村的少之又少,我们走访的结果来看,不到1%。而90后根本对土地没有什么概念,更不用说去种地了。70后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支柱,呆在农村种几亩地,怕是无法支撑一个家,绝大多数70后子女都在15岁以上,正是需要用钱之时,在地里是刨不出这些钱的。60后都在50多岁,大多数都承担了给儿辈们照看小孩的重任。
笔者统计了湖南湘中望城县某行政村人口结构表(见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40岁至60岁以下的人口总数人,占总人口数的33.%,具有从事农业生产能力的男性只有3人,该村水田面积约亩,人均需要种植水稻7.亩。但笔者调查发现实际从事水稻种植的不足50人,人均需要种植水稻3亩以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40岁以下的无人种植水稻。
表1湖南湘中望城县某行政村人口结构表
第一场变革: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合作社数量,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至年6月底为家,成员18.9万人(户),占总农户的13.%。而截至年底,全国范围内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了98万家,农户达7万户,占中国总农户约1/4左右,经营在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为87万家,平均规模00亩的家庭农场达到87万家,还有30万家为各种各样的产业化的经营组织,其中包括1万家产业化龙头企业。显然,湖南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赶上全国形势,至于这里面的水分含有多少,也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白,那就是农民已经自主或不自主地组织到了一起。
湖南合作社的发展大约分为两个时期。一个为自主发展时期,主要是一些种植户因共同的需要或不同的需求自发地联合到了一起。一个为不自主发展时期,主要是因为一些官方的需要或出于某些目的需求自发或不自发地组合到了一块。自主发展时期,农村合作社的数量相对较少,规模也不是太大,耕种的土地也不是太多,在农村中也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因此各界批评之音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都是乡里乡亲的本村或本乡人,联合在一起互帮互助,对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起到了不少积极作用。不自主发展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演变成了农民合作社,两字之差,意义就有了大不同,在政府和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合作社数量激增,规模也不断放大,实际或不实际耕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多,如保靖(年官方数据农民合作社全省第一)、平江、醴陵、常宁、湘阴、望城、宁乡、汩罗、浏阳等县(市)60%以上的土地都集中到了合作社名下。由于牵涉一些利益,特别是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外界的质疑、批评、抹黑都接踵而至。
尽管农民合作社有太多的质疑,笔者相信农民合作社是发展生产力水平的需求,是农村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是带领农民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一场关于农村土地的大变革正在到来。
第二场变革:取代农资渠道,一切利益归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的兴起,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农资传统渠道,特别是盘踞乡村多年的零售商。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暴风骤雨,心好者也死,心黑者亦亡。其结果,似乎一夜之间把几十来形成的农资传统渠道,打得个落花流水,零售商关门大吉。显然农资传统渠道,是被合作社(种田大户)取代的或者就要被合作社(种田大户)所取代。这不难理解,传统的农资市场或者说农村经济,信息不流畅、交通不发达、物资不畅通,农资流通的渠道只能是自上而下流动,经销商、零售商经营什么,农民就消费(使用)什么?买贵了只能骂几句或争论几声,买便宜了自个乐。合作社把农民组织到了一起,花钱的事自然就有了商量,一商量就明白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以前都太黑了,一瓶药赚好几块,一包药赚好几倍。而种植大户对种植成本就比较敏感了,一亩地多花1元钱,1亩地就得多花1元,这还了得,至少咱得进城跟经销商打个交道,了解一下行情吧。这不,大多数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都跑城里来与大农资经销商询价购货了。城里人都狡猾,咱得多个心眼,先上熊大家询个价,再上熊二家探个底,最后上光头强家砍个价。哇,一亩地要省好几十块啊,这种1亩地,都能省出个小面包车出来啦。
实际上,还有一些零售店正在顽强地生存着,化肥资金需求大,利润薄,价格也很透明,统防统治组织不愿意做,同时做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所以做的人相对较少,相比之下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做农资比较早、手头上资金也比较宽裕的零售店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懂些技术,做点除草剂或者蔬菜药,日子也还过得去。种子的流通渠道依然是县级经销商到零售商到农户,有些种子公司也跟一些大户直接打交道,但实际运营过程中问题和困难并不少,主要原因是种子销售季节过短,直接跟种植大户打交道人员配置需求过大,运营成本较高,一些种子公司尝试跟肥料企业或农药企业联合,但目前进展都相对缓慢。所以,种子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以传统渠道为主。种子的利润主要在终端零售店,一些经营好水稻品种的零售商,日子还算红火。
第三场变革:统防统治,糟得很和好得很很多地方的零售商甚至经销商把一切怨恨归结于统防统治组织,认为“万恶”的统防统治披着政府的外衣,拿着政府的补贴残酷地把他们逼上绝路。历史总有其诡异之处,湖南的统防统治兴起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基本属于同一阶段。湖南统防统治至今还在饱受争议,而江西、湖北、安徽、广西的统防统治正在紧跟其后成燎原之势,山东、河南、江苏的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也如火如荼。
统防统治组织出来啦,你别介啊,别上经销商那拿货啦,你在我这拿货,我都帮你把肥施了、药打了、虫灭了、病防了、草除了,出了问题我还赔!合作社(种植大户)一看,得,有这好事,咱跟他走。在统防统治和合作社(种植大户)的两面夹击下,头等的零售商也搞起了统防统治了,门面也从高家庄搬到省城了,二等的跑到县城干批发了,三等的跑到乡镇跟着统治统治组织干了,四等的买点杂货还维持着日渐凋零的农资生意,五等以下的零售店直接关门向合作社(种植大户)投降了。
年我们开始在县城、乡镇、村集对统防统治进行调查时,听到许多渠道商的意见,从市级经销商到村集零售商,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统防统治糟得很”。即使是统防统治做得还不错的人,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舆论的压力,也闭眼一想农村的情况以及搞统防统治受的“泥腿子”们的气,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思想超前的人也只是说:“尽管存在些问题,但这是农村发展的必然。”对于目前这种状况,认为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农村的民主集体力量起来打翻农资渠道的传统势力,乃是农民倒逼农资企业、渠道经销商进行自我变革的浪潮。传统的农资流通渠道,农民购买什么药、什么价格渠道商说了算,效果好不好,也是渠道商说了算,收成好不好,还是渠道商说了算。农民购买了好的农资产品,丰收了,赚了钱是运气好,购买了伪劣农资产品,减产了,绝收了,那是他倒霉。统防统治减少了农民的用药次数,以前种水稻早稻要打3~4次药,晚稻要打5~6次药,有的时候打稻纵卷叶螟要打上3~4次。统防统治大大减少了水稻打药的次数,现在早稻次,晚稻3次,中稻3~4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增加了农民的收益,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生态安全得以优化。以往个体农民喷洒农药的利用率不足30%,通过专业化组织统防统治后,利用率提高到60%。湖南的农药用量由原来的每年8万吨,降低到现在的5万吨一年,到年这一数字还在大大降低,这是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四十年乃至农耕文明以来未曾有过的功勋。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的言论明明是站在农药生产企业、传统经销商利益方面来反对农民组织起来,明明是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保存传统农资流通旧秩序,阻碍农业高效化、生态化、环保化发展,每个从事农资事业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附和。
第四场变革:政府采购的“过分”问题近年来,农药政府招标采购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政府采购农药给农民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实惠,在降低成本、减量用药、提高用药安全、避免使用中毒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利民利企的政策,却得不到任何叫好声。生产企业抱怨中标价格低,利润薄,资金到位慢,运作费用高(你懂的)。渠道商骂声一片,显然政府采购农资(药)发放给农民,缩小了市场份额,动了经销商奶酪,这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还不至于要骂娘。政府不要钱发药,这样的好事,农户却骂娘,这是怎么回事呢?政府采购的农药发放渠道有的是委托经销商发放,这好比让猫去发鱼,谁不干点雁过拔毛的事?有的是经过农技站去发放,农技站就那么几个人,哪里有工夫去送药?药最终发给谁了?有没有发下去这就很不好说了。当然还有发给统防统治组织的,也有发给种植大户的,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政府采购的“过分”到底在哪些方面呢?招标、中标环节这里不便多说了,反正你懂的,中标的也好,不中标的也罢,反正出来混,你就得按规矩来。政府采购的“过分”主要集中的发放环节,农民有的时候领到的药,根本没有用,因为错过了季节。有的时候被掉了包,药是发了,但发的都是一些过期的农药(这显然不是政府采购回来的)。更过分的是一些政府采购的农药,又回流到了渠道,甚至一些H省采购的农药,到了千里之外的G省流通,对传统渠道造成了很大冲击,这是生产企业、经销商说的“过分”。
第五场变革:土地流转与圈地运动据农业部统计,截至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6%,比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01年流转的土地面积比上年增长34%,年比上年又增长了40%,高速增长的土地流转数字背后的真相到底怎样?
合作社不虚报点流转面积,那不都不叫合作社。合作社流转面积一方面来自上头的要求,上头要求报多少,我们就报多少。另一方面来自理事长的当地人源、人脉,签个合同就算是流转过来了,再给点农药、化肥什么的或者一条烟算完事,地还是该谁种谁种。土地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转,谁也不知道,也无从核查。当然要真正查一下还是可以查出点问题来的,土地流转合同,农药、化肥、种子、农机采购合同,购货发票等审核一下,还是会有不少合作社要打回原形的。玩这一类合作社的群体,大多数是有点余钱,但并不是太多,也不愿意进城打工或做点生意,种几十亩或百把亩地,平常把上头的关系理顺,每年能轻松拿上十几万到几十万的补贴,也算不错。
咱们干的是现代农业,一两百亩地算什么,至少要成千上万亩。有些地方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甚至出台“招商引资”政策,给企业流转土地大量补贴奖励。土地流转了吗?流了,流转了干什么了,不知道,干得怎么样?也不清楚。介入现代农业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财大气粗的实体企业,反正不缺钱。政策一引导,一头就扎进来了。另一类是上头关系比较硬,能拿到的政策、补贴一样都不会少,地里赚钱不赚钱,不重要,甚至地都可以荒在哪里。
土地流转中还活跃着一部分人群,我们可以称之为土地经纪人,蛮有能量的,手下有几员得力干将,能高效处理农村事务(农村有些事,你们懂的),从农民手上把土地集中起来,然后再转给专业种植户,当然专业种植户也是需要他们解决不少问题的,他们流转的土地有的甚至达到了几万亩的规模,由于这部分人,行事低调,几乎不与政府有太多联系,属于土地流转中的隐形土豪,通常转手行情是50~元/亩,手上有几万亩地,轻松赚上几百万不是问题。写到这些,笔者满脸都是泪,我们干农资的买农药一亩地也就收元左右,还得提供服务,出了问题还得赔钱,一年累死累活,连人家零头也赚不上。还有一部分是米厂的老板日子也比较艰难,一年也要加工成千上万吨大米,到粮仓拿谷也是一件需要运作的事,还不如干全产业链,自己种上几百上千亩地可能更有奔头。
第六场变革:耕种者的真实摄影赵老爹今年60岁了,儿孙们都在城里,自己在乡下种了50多亩水稻,地都是亲友、邻居的,也不要流转费啥的,自己收了水稻后送两袋谷子过去。种植的是一季稻,黄华占品种,种子50元/亩;除草自己打的,包括田埂50元/亩。施药包给了打药队,4次药包打元/亩;化肥元/亩;旋耕、收割都是使用农机,50元/亩;浇灌条件还比较好,管水不要操什么心。不算自己的工钱,每亩生产成本约元。黄华占品种比较好卖,成熟了直接就有人到地里收湿谷,~10元/50kg,比送粮库要低一些,但省事,不用去晒谷、找车、排队。年成好可以收到kg,大多数时候也能有kg。每亩毛收入有1元至0元,去掉成本,每亩可赚~元。核算成本(种子50元/亩、除草50元/亩、化肥元/亩、农药元/亩、旋耕10元/亩、收割元/亩,共元/亩,赵老爹都是付现金,不欠账,投入3万多元),50多亩地一年可赚3万多元,比在外面打工还自由。
钱大伯50多岁,上有80岁老母,儿子已工作但尚未成家,家庭压力还是蛮大的。到外面打工,又照顾不到家里,租了村里00亩地种水稻,土地租金kg谷子一年,通常折合元钱。农村里转包别人的地都是按谷子计算的,谷价高自然租金也就高一点,谷价低租金也就少一点。由于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成立合作社,自己种什么,怎么种也自由一点。品种黄华占,种的一季稻。种子自己留的,合计30元/亩,施药是统防统治组织包了,90元/亩还包除草剂,出了问题还负责到底。尽管心里不放心,但还是签订了合同,谁让人家价格低呢。化肥到城里找批发商磨了不少工夫,折合10元/亩,还包送到家,不过货到了就得付钱。旋耕80元/亩,可以收了谷子给钱;收割机是外地的,下田前就得准备好现金,元/亩。打药自己来,另外叫3个帮工,老婆帮忙配药,4个人一天差不多可打多亩,天可以干完。请的3个人00元一天,管中饭外加一包10元的烟,折合每次打药8元/亩;除草(包括封闭药)加上杀虫得打6次药,打药工钱折合48元/亩,工钱得一天一付;管水条件还算不错,但每年也得花10元左右/亩的油钱。每亩生产成本:种子30元+农药90元+化肥10元+油钱10元+工钱48元+旋耕80元+收谷元,共计元/亩。谷子收了晒干后送米厂,可以达到~元/50kg。原来对晒谷比较忧愁,而且晒谷差不多要花到10元/50kg成本,现在村里的合作社有了烘干机,乡里乡亲的,人家也就收个成本价6元/50kg,不过来回运费和送粮的车费以及其他一些开支差不多要合到5元/50kg。由于种田多年,经验还比较丰富,钱大伯平均产量烘干后在kg/亩,减去付租金的kg,每亩地毛收入1元左右。种子自家留的,可以不用花钱,农药90元和旋耕80元可以赊帐,其他的78元都得给现钱,种00多亩地,需要投入6万元,大多数年份都可以赚到10万元左右。一想到儿子成家要花不少钱,钱大伯总要叹上一口气。
孙大叔40来岁,是村里的能人,成立了合作社,流转了多亩地,土地租金元一亩,年前就得付了。村里人都会算账,自己种也就赚个七八百元,流转给人家孙大叔纯拿元,粮食直补啥的还照样能拿,蛮合算的,不少人都想把地流转给孙大叔。按国家政策孙大叔只能种双季稻,早稻机插育秧软盘需要5张/亩,6元/张,国家补贴3元/张,按3年折旧,每年5元/亩,基质土5元/包,每亩大田需要用8包,成本为00元/亩。另外,播种、摆盘、苗床管水等需要5元/亩。孙大叔用的是简易钢架大棚育秧,长宽高的规格为30m×6m×.m,总造价为元。孙大叔亩的大田,需要5亩耕地作秧田,简易钢架大棚的总造价则需要90元。按10年折旧计算,每年平均成本为9元,每年大田用秧育秧成本为18元/亩。实际上在湖南这样的简易钢架大棚只能育一次秧,晚稻由于温度高,管理起来很不方便,还不如在大田育秧方便。种子用的杂交稻种子,60元/kg,每亩用1.5kg,种子成本需要90元/亩,两季元/亩。施药包给了某统防统治组织,早晚两季5次药,只要55元/亩。施药孙大叔雇用当地的人,8元/亩/次包干,不管饭,早晚两季5次药加除草次,一共7次药,工钱得56元/亩。除草剂早晚两季大致是40元/亩,统防统治干不了这个,孙大叔只能自己在经销商那里购买,一手钱一手货没有人敢赊账给孙大叔,主要是很容易闹纠纷。化肥是几个合作社一起跟厂家直接订,冬季就打款,据说合到元/亩。亩水稻,管水也是个大问题,每年孙大叔得花不少钱抽水浇灌,算下来每亩需要15元。旋耕机孙大叔用收割机和别的合作社换工,成本也不好计算,权且按市场最低价格计算。最让孙大叔头疼的是工钱是一笔不少的开销。田里的事情都得请人干,现在工钱也贵,只要一出工,半天就得元,一天就得00元,哪怕半天只干了1个小时的活。孙大叔的工钱也是一笔糊涂账,该花不该花也没有个数,大致整理了一下打药、管水、运秧、修渠、看烘干机等怎么也得90元/亩/季。烘干孙大叔自己建了一个烘干车间外加一个仓库,现在不愁谷子没有地方晒,也不怕粮食价格不好,价格不好时放在仓库,价格好时再卖,自己算了一下烘干成本约4分钱一斤谷,折合40元/亩,孙大叔每亩用不了这么多钱的烘干费用,因为他早晚两季每亩搞不到1吨谷子,前两年产量有了蛮大的提升,可以达到双季斤。
李大哥从美国归来,30来岁,年轻一切都好。李大哥创办了农业公司,流转了5多亩地,并签订了15年合同。公司开业之初,李大哥壮志凌云,要把美国的先进农业技术传播到中国,公司要上市,要做全产业链。李大哥的地租是元/亩。拖拉机、旋转机、插秧机、连栋5层摇架立体钢架大棚、播种机、收割机、烘干车间(日烘干能力吨)一样都不少,租了原来一个老粮库存放粮食。据李大哥自己说,一次就投入了多万。别的咱先不说了,先说说连栋5层摇架立体钢架大棚吧,4亩地可育1亩的秧,李大哥用0亩地建了0平米连栋5层摇架立体钢架大棚,总造价万。李大哥按公司化管理,请了总经理、生产厂长、财务、出纳,每亩还设立了一个生产经理,农机部还有一个部长,两个固定操作手,由于领导多,做事的人少,所以扯不清的事也比较多,总经理年薪0万,生产厂长年薪15万,每年李大哥放给固定人员的工资、费用最少也要00万,平摊到每亩地的工钱就得元/亩,这还不包括临时工。李大哥刚开始年年要跟种子公司、农药供货商、肥料供货商扯点皮,要不怪种子公司种子不行,要不就去检测肥料看看是不是假货,要不怪农药供货商配方不到位,反正事挺多的。后来,大家都不和李大哥合作了,李大哥才真正知道种几千亩地不是那么容易了。现在施药李大哥承包给了飞防公司,包药包工30元/次/亩,早晚两季打5次药,元/亩,不用管吃、管住。除草承包给经销商的打药队,40元/季/亩,包药包工包效果。不算管理人员工资,不算租金,正常李大哥种两季总成本/亩,这算是比较低的,只是如果把旋耕、拖拉机、插秧机这些设备的折旧、保养和维修算进去,李大哥的实际成本就远不止这个数了,再加上土地租金和管理人员工资元/亩,李大哥每年至少要拿出万流动资金才能使5亩地转起来,这还不包括基建费用。李大哥手上的钱每年越玩越少,银行的贷款也一直是延期和变个手续,有的时候连利息都支付不了。年李大哥公司自主种植面积压缩到1亩,总固定员工控制在5人以内,农机对外出租,只租机器不租人。其他0亩按元/亩再次转包给专业种植大户种植,公司提供农机、烘干、仓储和代收粮食服务。早几天,李大哥打来电话说,今年应当不会亏钱了。只是笔者在想,李大哥要实现赢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个真实的耕者缩影,众所周知的原因,人物都做了化名处理,但数据和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也许有些耕者的成本还要比这高。50亩以下的我们称之为散户,都算不得种植大户,这一部分人耕种绝对不是他们的主业,也许有一天他们就不干了,应当是真得干不动了。00亩左右的应当是耕者中的主力,他们必须赢利,因为这是他们的主业,他们承载者一家人的希望和生计。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或者合作社,我们确实很怀疑他们的赢利能力,但确定有大部分群体还是能保障田里的收支平衡。赢利或者说收入取决于耕者背后的力量,那些事情各位都心知肚明,只是将来政府的钱可能不那么好拿了。上千亩的耕作者很少有从田里赢利的,他们的成本主要是管理人员费用过高或过度的机械化。我们也能清晰地认识农业的未来必须是机械化,但目前至少未来好多年,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依然还是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合适的机械,而是因为利用率太低,运营的成本太高、太高。当然我们也相信有极少一部分上千亩的耕者还是赢利的。规模化、土地集中、土地流转在中国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00亩和50亩耕者的成本区别是租金增加了,其他的成本都是大大下降。我们调查发现,00亩左右的耕者,都是以一季直播为主,尽管种植两季会分摊掉土地租金,他们都没有去指望国家的补贴,尽管他们太需要一些支持和关爱,他们只是努力地耕作并赚取一些并不是太丰厚的收入。00亩耕者与亩耕者的成本区别是后者需要大量的机械化投入和雇用人工,当然他们不去拿国家补贴,一季稻直播成本会降低很多,但地里的收益也不会增加很多,因为机械的利用率一旦太低,成本就会大大上升。我们还没有见到能玩转5亩地的耕者,就算亩都鲜有人能玩转,因为管理的成本是根本无法量化的一个值,有的人1个人能干3个人的活,拿个人的工资。但现实中,有多少这样的员工让你能有福气找到呢?或许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才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吧。
第七场变革: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还没有官方统一认定标准,一些资料和文件中解读如下:一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二是适度规模土地,面积有一定的要求,一般在亩以上;三是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除了土地规模外,我们认为另外两条基本都做不到。另外再加上一条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基本就没有人会符合了。显然家庭农场不是单纯的初级生产者或种植者,应当是有较高生产力水平而且具有经营能力的主体。
回到我们前面的调查,一个1多人的行政村,大约有亩左右的耕地(稻田),以当前的生产格局,每个家庭耕种5~10亩,需要00~人在一定的时间段专门从事或参与生产。如果分割成00亩一个运营或生产单位,那么大多数行政村需要10个经营单位即可。耕种00亩水稻,插秧、打药、收割需要雇工外,平时1~人完全是可以管理过来的,那么1个行政村最多需要50人从事生产即可,而且这50人还可以互助、联合、联营。土地的集中会促进农业服务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也会促进土地的集中。政府之手应当扶持农业服务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而避免农业机械化的投入过度和利用率低的问题。1个行政村有1~个集农机、农药、农技、金融、保险、烘干、仓储的农业服务组织,那么支持0多人进行专业的农业生产并不会存在问题。
实际上在湖南不少地方,特别是城市的周边,家庭农场的雏形基本形成,如不少农家乐应当就属于这种性质。另外,一些葡萄种植户也是以一家人为单位,长期固定租用一部分土地进行种植,搞一些采摘活动,酿制一些葡萄酒。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种植水稻还没有见到,显然这与水稻的经济价值不高、运作空间太小有关。家庭农场要解决水稻无人耕种的问题,还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毕竟利益才是最好的驱动力。
第八场变革:关于农业的十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职业农民培训
职业农民的培训似乎搞了好几年了,且不说成效怎样,参加的次数多了,农民也疲了。现在要农民来培训首先会被问的是有没有饭吃,喝什么酒,甚至不少地方还要工钱和发烟,好像这培训是求着他们去参加的。听起来,农民素质依然很低。
事实是这样吗?很多老师根本没有下过田,讲起课来云里雾里,农民根本听不懂。一些培训组织者,为了增加人气,一些非农者也来参加培训。时间上安排有的时候也存在问题,农忙的时候,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只能委托自己家人或者根本不相干的人来参加一下,自然也就不会认真听了。当然不少地方职业农民的培训开展得不错,确实让不少农民受益。
第二件大事:土地流转
湖南的土地流转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引导的土地集中,一些村甚至流转率达到了50%以上。这些流转对实行农业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农业经营集约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然而对农业产出率基本没有任何提高。毫不客气地讲,这样的流转除了浪费大量的资金投入外,对粮食安全生产和保障耕地红线作用甚微。另一种是农民自发的土地转租,通常是转租给村里的邻居或亲友,还有是通过土地流转经纪人进行转租。乡邻之间转租的面积约在亩以下,通过土地流转经纪人进行的,通常都在00亩左右,这一部分的转租实际上也是土地流转,只是稳定性较差,年成好赚到钱了,次年也可能不干了。年成不好,亏钱了,第二年没有本钱干了。由于这一部分人没有享受相关的政策,所以自然统计中就缺失了这部分数据,实际上这个数据很大,湘北有的村甚至达到了90%以上,湘南一些山区这样的情况也开始出现。
第三件大事:土地流转经纪人
湖南活跃着不少这样的一些群体,拿着厚厚一叠合同在农村里转,收村民手中的地,然后再找种植大户来种。这些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土豪”,据说有的土地流转经纪人手上有几万亩地,一年赚个几百万没有问题。土地经纪人不仅是简单收地、转租,还做了不少利于和谐的事情。
第四件大事:粮食收购代理人
粮食收购代理人是我们的一种文雅的叫法,实际湖南没有这个称呼,这群人叫“粮贩子”,精得很,会搞秤。乡镇级粮库撤销了,创造了很大一个市场。一方面农民送粮不方便了,几亩地都不够一车谷,自己送划不来,装个车,排个队都没有几个钱了。另外,一些种植大户没有地方晾晒谷子,直接从田里把湿谷卖给“粮贩子”省事。“粮贩子”们一般上午收一车,下午收一车,忙的时候也有会收上好几车。通常30吨的车,装一车有6元的毛收入,扣除油钱、装车费还是很有赚头的,如果赚点农民的秤,那收益还要大。有能耐的“粮贩子”能调动几十台渣土车收粮,不怕吓着你,一年收几万吨的都有。
第五件大事:经营权抵押贷款
经营权抵押贷款这只是听说过,还真没有见到有人办到过。政策实施的细则还没有出来吧,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
第六件大事:农资电商
农资电商这两年发展很快,特别是年,传统的农药生产企业,不建个网站,弄个APP,那就落伍了。农资电商唱好的也有,唱衰的也不少。反正大家一个观点,农资电商对农民有好处,你看原来你买的农药要经过厂家到业务员再到经销商再到零售店再到你手中,价格不知要翻几倍,现在厂家直接给你供货,价格大大地便宜。
首先,我们来算下账,农药业务员到底一瓶赚了多少,通常一个厂家业务销售额就是万左右(当然有业务能力强的,做到上千万的都有,但毕竟是少数吧),农药厂家业务员一瓶赚10%,咱按10元钱的成本算吧,给经销商就是11元,业务员赚一块钱多吗?万的销售额,业务员一年能拿15万的毛收入,这必须保证所有的货款按时一分不少收回,市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每天早上能按时起床,准时发短信给公司汇报,不请什么假回家看父母,最好是不结婚或不找对象,除去差旅费4~5万,好像1年拿10万块收入也蛮不错的,如果你天天坐公交,顿顿吃盒饭,夜夜住十几块的招待所,差旅费4~5万你是可以拿得下来的。
接下来算经销商的帐,厂家业务员不给你11吗?经销商赚5%,这个数字不是我瞎说的,是你们搞电商的人说的,好吧,就按你说的算,一瓶农药从经销商到零售商手上就成了13元左右。通常一个经销商年销售量也就00万左右,当然广东、云南有做上亿的经销商,现在我们不讲那么远,大多数县级经销商就是这个量。一个经销商一年赚50万还不多啊?那我们算下账,经销商得有辆车吧,有个仓库吧,门面可以不要,在家里就行,但总得有个伙计吧。养一辆车一年需要多少钱?3万元够不?仓库1万元行吧?伙计克扣一点,一个月给元,外加一些日常开支,一年4万块好不好?这不到10万就搞定了么?还净赚40万啊,知足了吧。如果你能在年底把零售商的货款百分之百收回来,不请零售商出去旅个游,不打点一些相关部门,那你确实可以赚40万。
零售商最黑了,13元进的绝对要卖6元了。算到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一瓶农药从厂里出来到农民手上到底翻了几倍,10元到6元,到底是几倍?所以,所有的营销不吹牛都会死。算算零售商账吧,看看这群黑心的人一年能赚多少钱?做农资的没有人不说做零售商好干的,不要本钱,不要技术,货有人送上门,卖不完退回去,还要请吃饭,还要搞旅游。1个村耕地面积大约是亩,多的有5亩。每亩用元农药,1个村大约是0~50万的市场容量。山东寿光一个村有上亿的市场容量,这我知道。好吧,一个零售店两口子守着,生意别人不跟你竞争,这个村0万的生意你都做了,一年也就10万块啊,请注意是两口子,好多啊!在这里,笔者要很没有素质、很没有修养的骂一句人,所有说农资行业暴利的人都是孙子,那些叫嚣着要打破行业暴利的电商更是孙子。
我们来看看农资电商的情况,厂家到电商平台到配送中心到服务站到农民,谁没有了?好像业务员的那10%不见了。那么新增加了一个电商平台来分利益,电商平台要拿多少呢?我们先看看年阿里巴巴的净利润是多少?阿里巴巴的净利润是46.8%,46.8%就是我们传统企业要交的学费,这笔学费还会随着竞争的激烈越来越高,那么,请问,你的低价基础从何而来?好吧,你们做垂直电商,就按你们说的厂家到物流公司到农民吧,那你的引流要不要投入,要不依靠传媒来告诉用户到你这来购买?产品的单一性如何解决?零散的配送如何解决乡村直达的时效性?当然,你还可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把在过去一年里面、两年里面、三年里面某地有多少农民购买了你的农药?1月份要多少瓶?月份要多少件?通过调出过去几年销售的数据,把农药配到附近的仓库里,等着农民下单。想法确实不错,但我们应当知道农资市场是动态的,随气候天气、种植结构、病虫发生、农药抗性都会发生改变,你怎么来进行合理的储备?
在这里笔者也没有全盘否定农资电商,做为新的营销渠道或者说营销工具,电商依然会有存在的空间,只是不会有我们说的那么大,也不会像别人说的那么小?只是随着土地的集中,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和增加,厂家到服务公司到农户的格局必然会形成,那么传统的流通渠道和现行的农资电商必将受到冲击,这一天不会太远。
第七件大事:电商农资
彩电不好做了,彩电下乡。汽车不好卖了,汽车下乡。反正什么快完了,就赶紧下乡。电商也不好做了,怎么办?赶紧下乡啊。咱下乡总得找个风口进去啊,吃的、穿的、住的农村好像都不好进,行的也玩过了。恩,农村嘛,农民吃、穿、住可以少一点,差一点,但农资总不能不用啊,年年刚需啊,况且农资渠道战线那么长,一定存在暴利啊,那就拿农资开刀吧。
电商的本质是如何把商品下乡,而农村、农民的本质是如何让农产品更好的进城。这意味着电商可以与农资同床,但注定要异梦。绝大多数电商还拿着传统的数据在看待农村,农民的大部分支出是用于购买农资,我们在农村呆上几天,就会发现这是错的。当然,农村的数据统计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由于“刷单”的存在,所谓的大数据实际上有些扯蛋。据说,某宝统计的数据表明,西部经济、交通不发达的地区,网购的比例还很大,专家们分析了好多原因,结论是不发达地区,信息闭塞,传统渠道利润大造成。搞物流的也很纳闷,我们都没有发几件货去啊,最后搞清楚了,不发达地区没有法律意识,随便给点钱就能借个身份证,这些人也不经常上网,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用来刷单最好。
商品下乡,方便农民这是件好事,那么电商是否可以实现双向流通呢,让农产品进城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案例吧。湖南炎陵的黄桃品质很不错,每到收桃季节,全国各地的客商汇集在此,当地旅馆、饭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生意都很好。今年,炎陵的黄桃大规模的上了网,刚开始线上元/5kg,水果店3~40元/kg,线上比传统水果摊的价格要低不少,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错,线上的销售非常火爆,不少人都加入其中,快递公司直接把车开到村里,在地头就能开单,包装厂家直接把箱子拉到地头,要几个拿几个,农民都不用进城去发货,方便吧!因为更多的人加入,导致价格的竞争,网上的价格挺不住了,线上和线下的价格差距大了,零售商一看水果不好卖,赶紧告诉批发商,批发商一听,赶紧反馈给收购商,结果收购商不敢收了。然后,炎陵的黄桃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滞销。有的人会讲,你这案例没有代表性,农产品可以策划高端,你看像禇橙、柳桃策划多成功,那你们别说你们不知道禇橙90%的销量是来自传统渠道,只有10%才是来自电商。其实,所谓的农产品滞销,很大程度是人祸造成,比如毒香蕉、毒草莓造成的消费恐慌,更多的时候是农民盲目跟风造成,去年大蒜价格好,今年都种大蒜,结果不是价格不行,就是滞销,这不是电商能解决的。这也不是政府调节能做好的,你的大数据再厉害,知道市场容量有多大,产量有多高,但你不能叫张三种、李四不种吧,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仓储功能,完善深加工布局。农产品滞销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网就能解决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查,那些天天叫着帮农民销售滞销产品的网站、媒体,真正帮助农民销售了多少农产品?
第八件大事:打药队
打药队的出现其实应当是统防统治组织组建的,后来发现包药、包打出了问题扯不清,就不包打了,改为统防自治了。这两年,打药队卷土重来,只是他们不是为统防统治打药,而是传统经销商、零售商组建的,我们可以认为是传统渠道的一次反扑或者原本传统渠道就应当这样,这只是本质回归。打药队目前主要服务种植大户,包药、包打、包效果。传统经销商本身对农资有深入的了解,对病、虫、草害比较熟悉,对当地的病虫发生规律有一定掌握。打药队通常由经销商牵头,零售商参入,所以没有管理层级,不盲目地跨区作业,只是深耕当地市场,所以出现问题的很少。特别是新型机械的使用,如新型喷雾机械、植保无人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如新型喷雾机械3个人每天可作业00亩左右,无人植保机3~4人每天可作业亩以上。而且,打药队使用的是大包装,大大减少了农药包装物数量和成本,减少了废弃包装物对环境的污染。
第九件大事:第六产业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农业如果仅从养殖业环节来看,效益是不高的,但要把生产加工销售连起来,通过延长产业链,扩充价值链就可以提高效益。我们把它称为“第六产业”,“1++3”等于6,“1××3”也等于6,这就是国家层面对新提出的“第六产业”解释。
实际上,“第六产业”是在年代由日本农业专家今村奈良臣首先提出的概念,就是通过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
第十件大事:综合服务公司
农药、种子、化肥、农机、农具、农技、金融、保险集成化专注农业领域的综合型服务公司正在湖南萌芽。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农资流通或服务领域就会和国外一样,制造商到专业服务公司到农户,只是全方位地整合或链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愿他们一路走好。随着土地的集中必然促进农业综合服务公司的发展,显然农业综合服务公司的发展和完善必将更好地促进土地的集中,从而大大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产出率。
我们花两年多的时间调查湖南农业的现状,这只是湖南农村、农业的部分缩影。对于我们从事农资行业的人来说,农资不是夕阳产业,也不是传统产业,有的是生生不息的创新与对旧模式的颠覆。未来我们农村、农业、农资、农民都将经历非常痛苦的转型和升级,我们认为起码超过一半的人会在这场运动中离场,但是留下来的人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农村、农业、农资、农民,祝愿和希望大家在这一轮运动中胜出!
(全文完)
注:本文作者斗笠哥,真名刘杰,农资行业实战派专家,行业资深观察者,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本文原载《农药市场信息》,本文转载时将标题进行适当调整。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